手机:13301889869
13918071666
传真:021-50805239 APP下载
APP下载
接触了几百个抑郁症家庭后,我对青少年抑郁有了深刻的认识
本篇作者 | 简老师Jane
应对青少年抑郁,要从根源上深刻理解

临床心理咨询工作让我看到一种趋势,心理障碍发生的年龄越来越提早了。我过去接待的心理咨询来访者中,有很多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现在呢,我接待的来访者中有大量父母带来的初中生、高中生。
从2019年开始,我受校长镜面老师之邀,在郁金香家长学校带领二阶段的网络共修课程。在与几百个抑郁症家庭深入接触后,我为被定性为青少年抑郁症的人数之多、抑郁症家庭对青少年抑郁的认识之偏颇,感到深深的震惊、无奈与悲哀。
一位孩子在初中,就被诊断为很疑似精神分裂,各种药物吃的无数,几年过去了,但现在除了躲在房间,不理睬父母,毫无起色。一位父亲,已经带孩子做过4次电击治疗,但仍然无法消除孩子想自杀的想法。当然,类似的案例还有许多。
我记得有一次在家长课堂上,我做过《从根源看抑郁的症状》的讲座后,有一位家长与我互动说:“我不想知道这些理论,理论我都知道了,我想要知道的是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怎么解决。”我想这位家长的想法代表了很多父母的心声。一件事情发生了,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只想快点解决问题——这也是大部分人面对问题时的思维路径。
心理学研究发现,面对重大负面事件时,人们在心理上会经历: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悲伤、接纳五个阶段。我想抑郁症家庭的成员,应该也都经历过如上的心理历程,只是每个家庭处在自己独特的阶段——有的家庭已经走向接纳与改变,而有的家庭还处在愤怒、讨价还价、悲伤之中。
何季颖老师邀我为郁金香阳光会写些文章,谈谈我对抑郁的理解与解决之道。我想来想去,开篇第一章,依然需要从对青少年抑郁的本质认识谈起。如果不能从根源上深刻的理解青少年抑郁,那么所有的方法与技巧都会成为无源之水,南辕北辙,刻舟求剑。
每一个青少年抑郁家庭首要的任务,是去标签化
20世纪中叶,随着整个西方医学的发展,特别是脑神经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人的化学递质跟神经电流跟大脑运作的关联。当时整个精神医学界都认为改变大脑的电流可以改变“抑郁”的状况。
20世纪中叶另一个大的发展是心理疾病分类与诊断系统,1952年美国第一部诊断与统计手册,也就是后来的DSM问世,这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用的“心理学界的圣经”。
在第一本DSM里面,Melancholy这个词,就被“Depressed reaction(抑郁反应)”一词取代了,用来形容一种很严重的情绪低落。最早的诊断标准说,这种情绪低落是来自于一种内部冲突和未知的生活实践,比如失业或离婚。
当心理学家在这边忙碌地分类,把精神疾病、心理疾病做分类时,制药公司也没有闲着,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些可以改善情绪的药物。于是,50年代时,镇静剂开始变得非常流行,它用来治疗焦虑症。当药物可以用来改变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和情绪状况时,就为未来铺了一条路,大家慢慢开始意识到可以用吃药的方法治疗抑郁症。

回到中国,在“抑郁症”一词出现之前,大家遇到“抑郁”这种感受时,都会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感觉——“神经衰弱”。遇到“神经衰弱”,失眠心悸的情况,医生通常会给你开营养神经的药,像谷维素、维生素等。
但这两年我们也被“科普”了——不存在“神经衰弱”,其实就是“抑郁症”。
这两年我们的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在纪录片中也提到了中国抑郁症增长的数字,是很触目惊心的。
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词来命名大家经历到的无力感、挫败感、焦虑感,尤其是在大城市。在北上广这些城市会有特别鲜明的感受,人们需要一个名字来命名自己的情绪体验。因为人也是创造意义的生物,我们不停在自己的经验中试图去总结出一些东西来,找一些词来描绘我们的感受。以我们今天在中国大城市里所经历到的压力,“焦虑”、“抑郁”这些词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出口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下人们所谈论的“抑郁症”确实有一些人为制造的成分,尤其是当我们从它背后商业利益的运作去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推动它的相关利益团体更愿意把“抑郁症”呈现为一种严重的疾病。
根据临床观察,越来越多的假性抑郁症正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之所以会这样,首当其冲的便是社会舆论的传播问题。由于近年抑郁症研究步伐的加快,我们在原有的内源性抑郁和广泛性焦虑基础上,定义了很多新型抑郁症:如青春期抑郁症、产后抑郁症、精英抑郁症等等。这些新种类的发现,让舆论广泛地讨论引用,但更多的是讨论危言耸听的高自杀率、高影响度,让人们对于抑郁症无法从本质上科学客观地认知,以为心情不爽到极点就可能和抑郁症搭边或者挂钩了。85%的假性抑郁症患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自我认同感,并且形成大量对抑郁症的错误认知。
在接触了无数个被贴上抑郁症标签的青少年家庭后,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精神科主流的论断,就那么轻易的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贴上了抑郁症的标签,从此走上了就医、吃药、试药、调药、迷茫、痛苦、避世、病耻感的道路;而这些孩子的父母,从此也进入了一种炼狱一般的生活。作为每一个个体而言,有时一个标签,就是命运的分水岭。每一个青少年抑郁家庭,首要的任务,就是去标签化。是时候深入探讨与重新理解青少年抑郁的本质了。

童年发展出的“假自我”,是抑郁的元凶
瑞士心理学家爱丽丝米勒在她的著作《天才儿童的悲剧》里就有探讨过抑郁与童年情感创伤的关系。她的主要观点有:童年创伤常常具有深远影响,也是造成成年后心理问题的主因,她反对给专家、医师等给抑郁患者开药,她认为药物会阻碍患者感受此时的感觉与体验,而那些负面的甚至是痛苦的感觉恰是联结患者悲惨童年的关键信息。
抑制抑郁的药物让你一时感到爽了,但是却使你更难去了解自己童年里柔弱无助的“情感体验”方面的事实真相。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用药的抑郁症患者断不开药,且常常总会复发的原因吧!

这本书,感兴趣的家长可以自行阅读
如果你忽略了个人在其自身的经历与遭遇当中所“独有的”感受与情感体验上的事实。那你是无法真正理解抑郁的本质的。
个人的情感(emotion)发展状态则恰是一个人抑郁的主要原因。抑郁症的状态表现为没有活力、对事物丧失兴趣、感受不到自己的真实情感体验,被挫败、沮丧、恐惧、痛苦与黑暗笼罩着,并难以从中走出来。
生理层面的化学生物上的激素、腺素所发生的紊乱更多是情绪状态失调的反映、而非其根源。就比如一些事情使我生气、激动而肾上腺激增,而感到血液上涌,呼吸急促、以及害怕后身体惊出一身冷汗。这些情绪背后都有生理上的化学变化,但是不能说这些化学变化是情绪的根源。恰是情绪才引发了生理的联动变化。
抑郁症的根本原因,在于童年创伤性情境导致我们必须要压抑那些在关键遭受上真实情感的反应,而当这些真实情感体验被压抑、遏制,以及对于糟糕情境的适应,人们就不能充分自由地发展自己情感上的自主性。
当我们并不被允许依照自己的真实情感做出反应,反而是被父母无意识的情感体制的要求、糟糕情境的压力所逼迫,就会发展出一个“假自我”。(这个假自我作为我们适应那个成长经历的固定的角色或人设。它帮助我们斡旋那些特定遭遇、情境与经历)。
而这个“假自我”在后来常常会发展成为一个我们将自身价值感所系于其上的“ego”,这个或者叫优越感、妄自尊大,或者叫营造的良好自我感觉,其存在的基础与依托是外界的认可,而非真实的自发自主的情感发展的状态。(我们真实的情感与需求由于早年处境当中的潜在遏制的缘故,其实并未真正随着年龄增大而随之发展。)
我们在头脑里为自己营造(且往往也父母老师配合着)的宏大的自我投影,(比如以学习成绩论英雄),并误认为这就是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当假自我在后来的生活当中因为现实的挫折、出现动摇、坍塌、瓦解的时候,(比如成绩不再优秀了),原本的虚假影像所掩盖下的问题就不免暴露了,抑郁的状态也就不免出现了。

当假自我解体与崩塌,抑郁便发生了
抑郁爆发最直接的原因常常是由旧的虚假的自大幻觉的坍塌所引发(比如学习成绩不再优、在同伴中被误解、被老师批评等),这些旧的自大幻觉由于借助一些外界的认可得以维系着,而真实的自我和情感发展程度的缺失与滞后永远是藏在其背后的问题。
在我们的文化里,由于特定原因,没有尊重孩子的权利、意愿、感受的习惯,所以很多的创伤其实被隐匿在了我们的文化习惯和语言方式之外(除了少数极端情况,比如被严重家暴等),而事实上,隐形创伤数量远比被揭露和公开讨论的极端情况多得多。
大多数孩子,或多或少都会被自己的父母所要求着,在部分父母本身的情感发展状态并未成熟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将太多的情感需要寄托于孩子去满足,当孩子的自我发展是以照顾父母的情感需求为核心时,这时孩子便难以表达及发展出自己的真实自我了。
为了维系与父母之间的联结,孩子会压抑自己的真实需要与感受,服务于父母的情感需要,在这种模式下发展出来的自我是一个以外界的目光和认可为依托的 ego(假自我)。它与那个依托于孩子自身真实的感受与需要而发展出的 true self(真自我)相对。

抑郁的发生主要就是在 ego (假自我)解体与瓦解的时候。此时我们常常意识到自己可能再也无法得到那些我们依赖着的认可,或者无法实现自己基于幻象而构建出的成就,以维持自己想要的外部形象。
这个时候,对于自小便活在父母(后来为老师同学等待所替代)的期待之中、并通过符合某些外在标准(比如学习成绩)而不断获得认可以维系自我感觉的人来说常常是难以承受的痛苦。此时自己的真实自我并未得到发展的缺陷就会暴露出来,在没其它的借助物以平衡那个失落的时候,抑郁必将接踵而至。
虚假的自大是对抑郁的抵御,而抑郁则是对那些深切的悲伤与痛苦的无意识的分离与抵御,当受创者能穿越恐惧(这些恐惧也是童年里的恐惧的延续与变种)触碰到内心压抑潜藏多年的真实的情感时,这个强烈的情感爆发常常会带来巨大的解脱。
因此应对抑郁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自己自童年里的情感世界进行发掘,将那些在创伤过程当中所压抑与分离出去的真实情感与合理反应(如被父母伤害时的痛苦与绝望、被剥夺时的愤怒、以及深切的悲伤等等)进行重新体验及宣泄,如此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
而对于真实自我遗失的持续性哀悼可算作是在抑郁之中进行治愈的过程,那些原本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情感在这个哀悼的过程中,能得到重新的生长与发展,许多的活力会重新从我们的内心生长出来。
要知道抑郁的反面并不是没有快乐这么简单,抑郁的反面是活力、是去体验真实的自己与情感的自由,哪怕这些情感是痛苦、是悲伤。纵使是悲痛,那也是我们真实命运里的重要内容,它是我们自儿时里的故事的重要真相,那些被自己的虚假的 ego所把持着的人必须要依赖源源不断的来自外界的认可与关注进行补血,只要那个ego持续得以被维持,他们就可以免于抑郁的困扰,但是也无法触及他们内心深处所有的真实的故事与命运。

抑郁症患者常常还会出现许多人际关系上的问题
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与价值观遗留的惯性,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看待事实的方式。在讲求以孝道为重的过去,我们并不鼓励父母给予孩子平等的对待,甚至默许父母将孩子当做自己的所有物,与财产几乎无异。
此时父母尊重孩子独立的情感发展简直是一个奢侈与例外,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滥用自己作为父母的权力,给孩子强行摊派自己的意志,进行情感索取,而社会并不将此当作错误或不当。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孩子们都只能妥协,无形之中背负着父母潜在的情感债务,并被这些背负所塑造着,当孩子逐渐放弃自己本来的自我表达,将自己的真实需要压抑下去,并努力扮演父母的要求与期许以维持父母的接纳时,可以说这就是假自我形成的基础。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内化的父母,当我们自小内化的这个父母没有给予我们的感受充分的尊重与理解时,我们也没有学会理解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当我们与外界互动、尤其是建立亲密关系时,其互动模式常常会重复着过去的创伤与缺憾。
在人际关系里缺乏安全感与自信几乎是所有抑郁症患者的通病,这些安全感及信任的缺乏恰恰是因为过去作为孩子时的真实感受并未被自己的父母所理解甚至所看到的缘故,因为真实的感觉不被接纳,压抑下去后所为维系的也不过是有条件的接纳,如此在后来长大后,为了获得与别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也会过多地妥协与压抑自身的情感需要。
越是亲密的关系,创伤遗留的展现则越是淋漓尽致,我们渴望向伴侣得到的,恰恰是我们自童年里就缺乏的东西。父母因为自身情感发展程度的原因,无法给予孩子无条件的爱,这甚至超乎了父母的意愿,因为也许父母本身也处在他们自身的童年缺憾当中不得解脱。

抑郁是我们这个时代社会转型的伴随物
在现代社会,适应不同环境和与不同人相处的方式成为了一项基本要求,人格缺陷容易显露。当环境出现变化、要求我们走出一种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时,抑郁的状态往往更容易出现(暴露),因为这样要求人们有一个独立自主的自我去应对斡旋生活的各种挑战。
我们文化里的习惯与价值观,无形之中所导向出来的并不是鼓励我们去拥有真实的自我,不是鼓励我们去认真对待自己的情感,而是否认自己的真实自我与情感。几千年以来的集体主义文化,要求我们的不过是去扮演好那个文化和群体所要求的角色。而现代化过程之中的中国,那些潜藏着的问题得以爆发,抑郁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
从神经系统理解抑郁症的症状
首先要强调的是,我们可观察到的抑郁症人群的悲伤、快感缺乏、厌恶感、消极回避,焦虑失眠,以及行为和生理反应(例如退行、失活、,食欲不振),我们称之为症状。药物治疗,主要缓解的也是躯体层面与神经系统层面的症状问题,而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躯体症状背后,神经系统运作的机制。
认知科学先驱阿朗•贝克彻底改变了抑郁的科学研究,他阐明了抑郁障碍的生物学机制,巩固了这种障碍的一些认知特征。贝克和他的同事基思•布雷德迈尔(Keith Bredemeie)发表在《临床心理科学》的一篇文章,形成一个全面的抑郁症理论依据。
贝克是美国心理科学联合会成员、詹姆斯•麦基恩卡特奖获者,他和布雷德迈尔吸收并借鉴了多层次的分析以及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临床、认知、生物和进化的方法——为抑郁症的症状学及其自身特点提供一个从诱因到痊愈的广泛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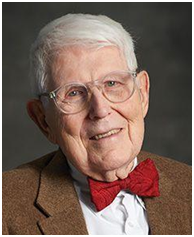
阿郎•贝克 Aaron Beck 2016
根据图一综合模型可看出,遗传风险和早期经历/创伤都有助于信息处理的偏差和生物应激反应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倾向会导致“消极认知三联组”的发展(即消极自我、消极世界和消极未来的信念)。
反过来,这些信念的形成和活化进一步加剧了认知偏差和应激反应。早期经历/创伤在消极信念的形成中起着直接的作用。升高的压力反应和根深蒂固的认知偏见导致了这些处在风险之中的个体对消极信念的信奉。消极自我 、消极世界信念和消极未来的信念,这三种信念的结合,贝克称其为“消极认知三联组”。当这些(例如,通过压力性的生活事件) 被激活时,这些信念触发了一致的情绪,如悲伤、快感缺乏、厌恶感、以及行为和生理反应(例如退行,失活,食欲不振)。
图一 抑郁倾向
根据图二模型,沉积的压力和消极信念的相互作用产生了消极的认知评价。如果个人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一项重要的资源,就会启动各种进程节省精力以补偿这种损失。
具体而言,这些过程包括:(a)消极自动化思维产生的认知和情感症状(例如,悲伤,自卑感)和(b)自主反应和免疫应答造成的“病症行为反应(例如,厌食症,快感缺乏)附加失眠症,进而导致消极信念的增强/加强。
一旦这一神经系统运作程序被激活,决定是否/何时终止该神经系统运作程序的因素有许多。这些因素包括:个体拥有的社会支持系统,个体思维心理认知的重构,以及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勇气与毅力。然而,消极的信念潜在地破坏了这些心理程序的运作,神经系统倾向于维持抑郁症状的相反的过程(例如:反刍思维、回避应对,心理冲突)可以对个体产生附加的应激因素。
图2 “抑郁项目”的沉积、表现和维持
因此,解决抑郁症状的关键,也在于解决三大拦路虎:第一,用正念训练缓解反刍思维的自动化运作;第二,通过心理咨询与正念练习帮助个体直面心理问题,增强自我接纳的心理耐受性与定力;第三,通过心理咨询与正念认知行为疗法,帮助个体改变负面消极认知结构,重塑思维与行为,尤其强调行为的规范化与结构化重塑。有关于正念心理疗法的理论与实践,在以后的文章中会进一步探讨。
个体如果处于应激状态下,承受力不足,在精神科医生的指导下,用药物缓解一下躯体化症状,是十分有必要的。但当个体处于平稳期时,父母还是需要帮助孩子直面问题,进行心理层面的干预。其实父母就是孩子最好的心理咨询师。
孩子求病的动机与求助的意愿
抑郁症的爆发,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在我们这样一个追求物质、成功与效率的时代,家庭养育、学校教育,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大背景,都在造病。
尤其是不合理的教育观念,更容易使家庭教育走向两个极端。一端是管束与强求,如强求孩子学习,强求孩子听话,强求孩子优秀。普遍的强求给许多孩子的心灵造成压抑,当压抑到了一个极限,就会爆发为反叛。有许多孩子在青春期,选择抑郁症状作为一种反叛形式,因为只有这个才可以打垮强硬无比的父母。
另一端是放纵与溺爱。在父母溺爱之下,许多孩子心灵幼弱,不敢与世界接触,害怕跟人相处,习惯于一个人呆在一个地方,发展出孤僻怪异的个人行为,使他们更加难以融入群体。强求与溺爱也表现为父母对孩子过度限制、过度保护、过度给予。我们的时代处处都是这样的情况。限制太多,让孩子经验单一、思维僵化、不知变通、缺乏应对生活多样性的灵活性。
保护过度,让孩子心灵幼弱、缺乏勇气、不敢尝试、更不敢有适当的冒险,但求偏安一隅。父母给予太多,如同过度喂食,让孩子厌倦,便损害了孩子求生向好的自然动机,甚至引起孩子强烈的反感,以致形成条件化反射:只要父母让他们做的事,他们都毫不在意地加以拒绝。
当他们出现了所谓的各种心理及生理症状,则把父母吓坏了,病急乱投身,于是,什么单向、双向、抑郁、躁狂都来了,医生开药,原生家庭理论,各种理论,十八般屠龙之技(自行百度含义),纷纷登场 .....
孩子躲在抑郁症这个病中,而这病,既是他们自己找来的,也是父母和这个时代制造出来的。父母一下子从过去的强求,变成现在的依从,对孩子过度保护,孩子便乐得呆在病中,苟安于一时、逃避以求舒适,他们不知道心理症状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更不关心他们失去的是什么。

说到底,这些孩子正在享受症状,还没有真正受到症状的拖累和损害,也意识不到症状最终会把他们的人生毁掉,因此并不痛苦,反而因病获益。这益处包括,在跟父母的关系里竟然占据了优势,可以沉溺网络游戏等。因为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也不肯接受心理咨询让自己有机会成长。他们大多处在“求病”的时期,还不大知道“求助”。或者说,他们求助意愿很弱,求病动机却很强,面对生活艰难(不管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如学业压力,人际焦虑等),他们急于找到一个“病”躲起来。躲都来不及了,哪里还想把“病”治好?
在这种现状下,唯有父母先觉醒,不再梦里造梦,不再用各种限制性的信念控制孩子自由的发展。而自我成长的第一步,就是接纳现实,如实地从现实出发。而不是再寄希望于种种屠龙之技与奇迹发生。
特别声明,本文观点属于个人观点。
后期,我会用一个系列的文章,进一步探讨青少年抑郁家庭如何一步步改变与成长。